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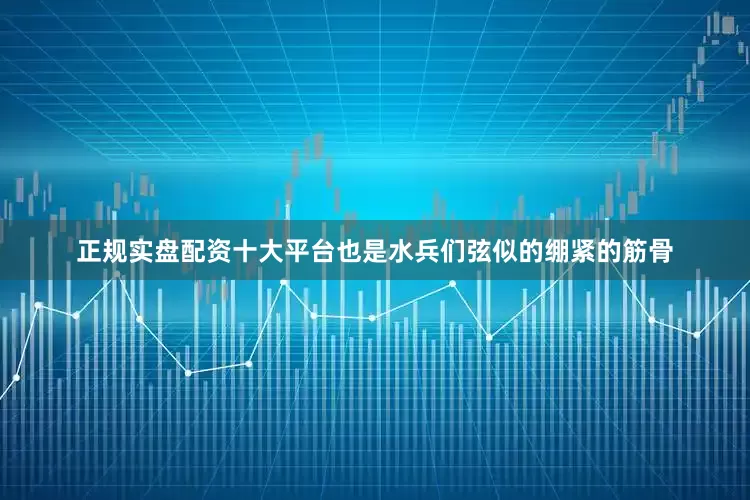
三叔每次从部队探亲回来,人未到,味儿先来。一股子海腥气,咸咸的,跟着他那身笔挺的海军军装,一块儿钻进门。这味道对我们闻惯了泥土香的乡下娃来说,新鲜,又有点冲鼻子,像大海捎来的口信。
我们稀罕地围着三叔转,眼睛总离不开他那身蓝,扣子亮得晃眼,肩章上铁锚神气。趁他喝茶拉呱,我总像小狗似的,偷偷凑近他袖口领子,猛吸一下,那味道直冲脑门,又腥又咸,厚重得堵嗓子眼,舌头根都泛出铁锈似的咸来。这味道,倒比三叔的模样记得还牢实。他走了,军装挂进衣柜,那股子咸腥气还在里头打转悠,勾得我常开柜门,把鼻子埋进去。小身子缩在柜子前,非要把这陌生大海的滋味,咂摸个够。那会儿只觉得,这味道像藏着什么秘密,又怕又馋人。
长大了,才咂摸出这咸腥味的门道。听三叔“侃大山”:夜里大风大浪跟黑山似的压过来,船像片叶子;跑远海,酸菜炖白肉吃得人反胃;船舱挤得慌,机油混着汗馊味,能把人腌入味喽。他抽着烟,烟雾裹着旧日的气息,慢悠悠飘散。听着听着,那咸腥味在我心里就有了画面:它成了甲板上风浪甩下的盐粒子,成了船舱里机油汗水捂出的“老陈酿”;是漂在大海上找不着北的孤单,也是水兵们弦似的绷紧的筋骨,这味钻进鼻子,一会儿变成防波堤上白花花的盐霜,一会儿又像碎浪尖儿上的亮光;是黑咕隆咚里船帮子拍水的闷响,也成了水兵们想家时偷偷咽回去的眼泪的咸涩。
展开剩余54%老话说,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。三叔到底脱了军装,复员回家。那身合体的军装和他挺拔的腰杆,都悄悄收进了岁月箱底。可有回翻他床底下的旧箱子,“吱呀”一开,那股熟悉的咸腥味,像被惊醒了似的,丝丝缕缕往外冒。
箱底压着发黄的老照片,照片里年轻的三叔立在军舰上,海风灌满了军装,身后海天茫茫。瞧他那只手,指关节粗得变形,是长年累月跟缆绳较劲留下的“勋章”。一到阴天下雨,他就爱揉膝盖,那是铁甲板的寒气、咸湿的海雾,给他悄悄刻下的印记。有时他坐那儿,眼神飘向远处,那眼神像藏着两片深不见底的海水,平静底下,隐隐翻动着咸涩的浪头。原来这味道压根没走,它早沉进三叔的身体里了,成了他身上一块洗不掉的“胎记”。大海的咸腥,在他身上熬成了礁石般的硬气,炼出了浪头也打不垮的韧劲。难怪人说,当过海军的汉子,像是被海盐腌透了骨头。
后来我去海边,独自站在码头上。海风卷着那股又冲又熟悉的咸腥气,劈头盖脸砸过来,像久别重逢的老伙计,猛地拍你肩膀。那一刻,我耳朵里仿佛听见沉重的锚链,在深深的海底“哐啷哐啷”响,我突然懂了,三叔身上那总也散不尽的味道,就是大海颁发给他的勋章,早烙进了灵魂里。
涛声还是那个涛声,日子哗啦啦地流。那海腥气,早已不再是小时候那个陌生又遥远的海洋标记了。它成了三叔跟风浪搏斗过的生命印记,深深沉淀在他的血脉里。长长的防波堤伸向远方,沉默而坚定,像道沉默的脊梁;而这咸腥味,正是时间这片大海,悄悄给我们每个人心里,埋下的一枚永远不会生锈的锚。
□朱明坤
(责编:刘洋)
发布于:山西省免费股票配资平台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